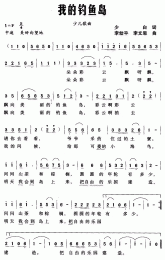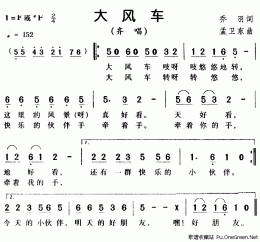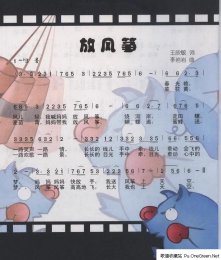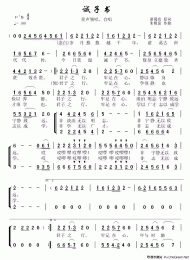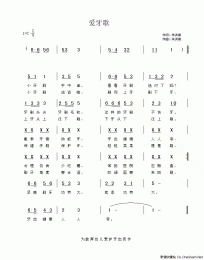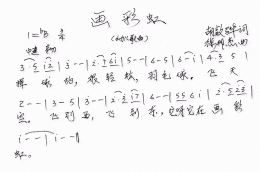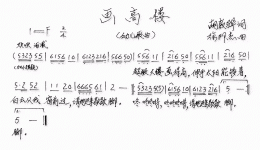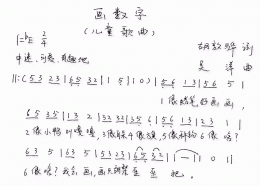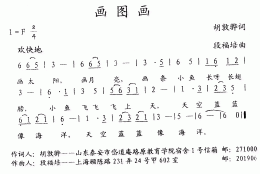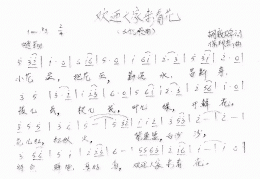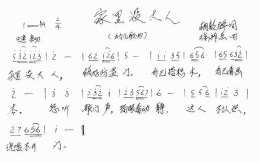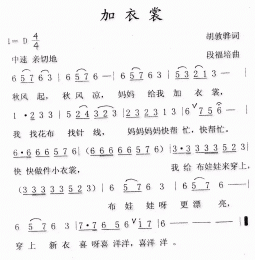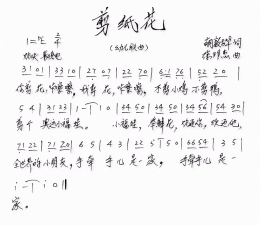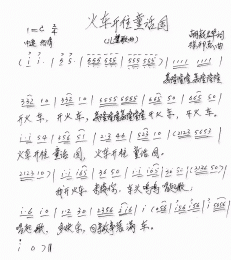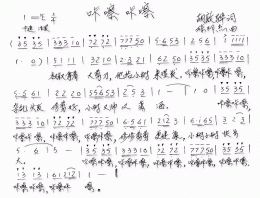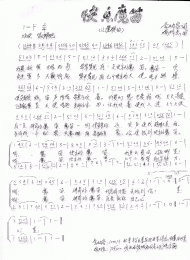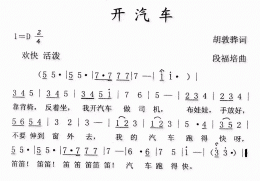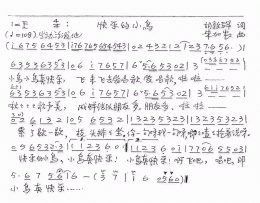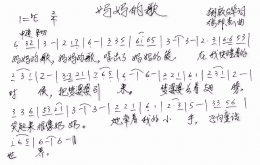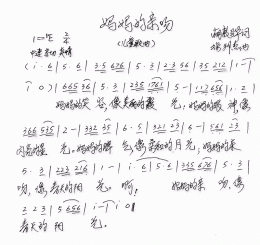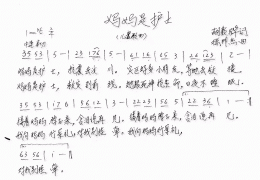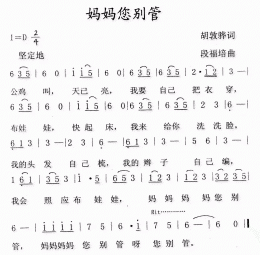美国精神病院真实事件(被迫入住精神病院时如何寻求帮助)
长话短说,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艰难、焦虑、麻木、疲惫,以及最后一根稻草的触发后,我终于决定寻求专业的帮助,并在半夜给学校的心理门诊打了电话。叙述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词让对方判断我有“迫在眉睫的自残风险”,于是她联系了警察,把我送到了最近的医院急诊科。
凌晨四点,我僵硬地把自己放在急诊病床上,抬头望着窗帘环绕的方形天花板。医疗设备发出冰冷而有规律的电子提示音,临床老人平静的呼吸夹杂着一些痛苦的呻吟,强烈的不真实感袭来。我试图入睡,但护理人员一直打断我。我向护士、精神病医生和一名完全警觉的警察重复了同样的内容,然后我被告知我要转院了。往哪里转?每个人都神秘地称之为设备。由于对美国医疗体系一无所知,我也不想再问了。保安拿走了我的随身物品和衣服,还在我手腕上戴了一个橙色的手镯,提示高度危险。从这一刻开始,我被正式限制了人身自由和隐私。
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原则在哪里?第五修正案哪里禁止自证其罪了?我没有网络,也不知道我朋友的美国手机号码。我怎么和外界联系?我怎么证明我不想伤害别人,我不危险?我怎么证明我没病?至此,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断的压抑缓冲了我应有的恐惧和警惕。我冷静的配合指令,让一切发生。
被搜身后,我被放回病房,穿着病号服和防滑袜招摇地在医院里走着。当我除了脚踏实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新鲜。我好奇地和其他病人聊天,护士们格外警惕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仿佛下一秒我就会分裂其他人格,扯掉电源线,绑架人质勒索他们放我走。但我并不想惹麻烦。反而因为占用了这么多医疗资源而感到不安。所以即使接下来的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把我绑在轮床上,把我推进救护车,我也没有质疑,只是想看看这个运行良好的预防系统还有什么花招。
在去工厂的路上,阳光明媚。窗外,四月的亚特兰大灯火辉煌,一切都充满活力,像万花筒一样慢慢展开,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就像车流的声音,我的心情被隔离在救护车之外,朦胧却保持着距离,无情地跟随着我。我不知道我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也不知道我会离开多久,但我不在乎。最可怕的死亡已经被我预言过很多次了,和医护人员呆在一起并不是此刻更可怕。
第一天
在忍受了漫长的等待和低效复杂的程序要求,签了厚厚一叠法律文书后,终于完成了非自愿入院手续。这家“精神病院”名为xxxx行为健康,在GA有18家类似功能的私立机构。当急诊科认为患者“处于伤害自己或他人的紧急风险状态”时,会推荐到就近的机构进行非自愿隔离治疗。我被分到一个相对平静的成人区,和其他自残但失败的人待在一起。
免费面积不大。有两台电视,两台座机,一些简单的卡片,填色游戏,桌游和桌游,几本没脑子的软文小说,还有其他无聊的病人。护士站位于区域中心,监控两侧的病房、活动室、咨询室和室外娱乐区。双人病房设施简单,空间足够宽敞,但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不允许关门,卫生间甚至用半个泡沫门隔开,方便医护人员在危险发生时及时介入。好在患者都是有礼貌有素质的人,心照不宣的不打扰对方的私人空间,大大减少了隐私被剥夺带来的不适。可能用于自行死亡的工具会被提前没收。铅笔、精装书、鞋带,甚至不必要的衣服、多余的毯子都是不允许的。窗户封得严严实实,家具固定在地上,不能移动。每扇门都必须用一把特殊的钥匙打开。在非休息时间,所有患者必须留在活动区进行监护。药房护士会检查病人的口腔,防止他们偷偷攒下当天的剂量。
px; text-align: left; margin-bottom: 30px;">我设法联系到了法学院的朋友,通知了她们我的现状。用分到的毛巾和病号服叠了一个枕头,很快入睡了。Day 2
精神病院每日遵守固定的活动表。六点钟护士粗暴地敲着并没关上的房门叫我们起床,测体温和血压。七点半列队去餐厅吃早饭。早饭定量供应,一杯果汁,一杯咖啡,鸡蛋、燕麦粥、培根或香肠、一块烤饼干。我不记得有多少天没有进食了,如此简单的食物也没什么可挑剔的。
我找了张桌子坐下,和旁边的人搭话。Miriam是墨西哥裔,黑色卷发挑染了红色,28岁的年纪已经养了五个孩子,第一任丈夫在墨西哥抚养她的女儿,拒绝让她们相见,她找过律师但没帮上任何忙。入院前她服用了大量药物,最后被家人发现时只能送去洗胃。她英语词汇有限,但还是尽力表达着对这里食物的鄙夷。坐在我对面的Natasha是个酷酷的黑人女孩,29岁,素食主义者,曾经是护士,个子不高,沉默寡言,一双大眼睛时刻审视着周围。每次她看到我陷入沉思的时候总会关切地问我是否还好。我所在的冷静成人组官方名称是“进步组”,这里的人如果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有伤害自己的风险。并不方便直接去问别人是怎么进来的,但既然时间足够,总能等到他们主动来分享。
小组活动时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Ben。一米九的个子,结实匀称的身材,佐治亚理工的大四学生,是我刻板印象中受欢迎的美国白人男孩的样子,似乎永远精力充沛准备去运动。像他这样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也会想要主动结束,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下午的日程是大家围成圈玩击鼓传花,几个护士学院的志愿者热情洋溢地鼓励每一个人讲自己最感激和最恐惧的事情,自称是来向我们学习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共情让我反感,好像身处动物园的笼子里被人观察着。
晚饭后来从“康复组”转来一位新的病友Miguel,23岁,墨西哥裔,会讲三种语言,带着眼镜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认真地和身边每一个人打着招呼。他在艺术学院学电影专业,疫情期间为了更好的工作前景而转去了金融行业。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或许因为他第一代移民的文化背景,让我可以放心地和他吐露我前二十几年在中国的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的离奇而魔幻的故事,而不必担心造成不解。说完后我问他你有什么创伤,原生家庭?童年阴影?中学被霸凌?还是遗传疾病?他诧异于我的直接,然后又尴尬地笑了一下。我解释说我并不了解你们的文化更欣赏哪类性格和品质,所以自然不知道什么人会被边缘化。他听完放松了许多,讲他母亲过于要强的性格、他父亲对他的打压和对哥哥的偏爱。幸福的人生往往相似,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我理解Miguel因为我们都习惯于过度思考和过度自省,保持清醒敏锐的代价便是接受真相的龃龉不堪,精神生活在高处,现实中就难找到落下脚的地方。有时混沌不觉其实是一件幸事。
Miguel问我是否想回家,我犹豫了一会,说我不想。我代入了《心灵奇旅》里找不到生活火花拒绝投胎到人间的22号灵魂,待在精神病院和来来去去的人聊天不就是同一回事吗,我乐意漂浮在外旁观生活。不同的是我还在收集素材,准备出卖他人。和Miguel的交谈一直持续到十点的入睡时间,我们感谢对方充当了彼此几个小时的心理医生。
Day 3
我不会生活,我过去的生活只是对其他人对社会规范的拙劣模仿。早起、为自己准备食物、通勤路上听新闻、学习/工作八小时、健身、阅读、听古典音乐放松、社交、安稳地入睡,做到这些好像我也可以变成一个普通人走在正轨上。可是我知道我只是在表演生活。很久很久以前我还有行动的激情,如今我只是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和植物一样等待终止。可我和植物的区别在于我有意识和感受,我会痛苦。
精神病院的日程很解压,与世隔绝,一日三餐和睡前零食,定时休息,参加小组活动,和不同的人聊天,偶尔在户外吹吹风。我不用计划下一刻应该做什么要达到什么成果。我也不用再逼迫自己走出舒适区,扮演不同的角色,满足他人对我的期待。在这个远离一切评价标准的地方,和一些以后再也不会相遇的人们待在一起,我反而感受到了无比的自由。时间、偏见、价值判断和种族身份都不再束缚我,在重复而规律的节奏下进行最基本的活动,继续活着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难了。
今天来了一位新病友Melissa,42岁的白人小学老师,女儿刚刚高中毕业,儿子本科学生物正在申请牙医学院。她治疗双相18年了,三月经历了母亲去世的剧烈悲伤后要求医生换药,可新药的副作用太强,导致她在浴室失去意识,不得不让刚成年的女儿送她去急诊。一说起入院她还是眼泪汪汪的想要回家,我尽力安慰她,等她情绪好些时开始絮絮叨叨讲起家里的猫猫狗狗,儿子的未婚妻,和小学里同样糟糕的管理。她说她现在充分理解了小孩子失去自由被管教时的抵触心理,出院后一定会更经常换位思考。
Adrian是一个高高帅帅的德国男孩,患有严重的焦虑症,每次和家里打完德语电话后总会焦虑发作,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休息,印象里从来没有看见他笑过。Aubrey则是另外一种引人注目,30岁,南方姑娘性格,张扬肆意,不拘小节,有一个3岁的女儿,习惯称呼所有人为baby girl和baby boy,热爱食物,无论是谁有多余的餐品她都来者不拒。从康复组转来的Twilight,28岁,长长的及腰卷发,甜美热情,忽闪着机灵的大眼睛跟我们讲没有新的病人入院他们是不会放走任何人的。David,gay,加拿大口音,银发染成了电光蓝色,说宁愿回监狱也不想和医院无能的官僚系统打交道。
晚上等待吃药的时候,Natasha突然问我是不是只有那种想法还没有实施,这里没人直接说那个词,我知道她的意思,于是点了点头。她定定地看着我说你很幸运,因为一旦实施但没有成功,你就会不断地回想那个场景,变成之后的噩梦。我知道她作为护士自然很了解那些药的用量,如果她没有如愿一定是意外中的意外。我说我很抱歉她的遭遇,仅此而已。我不能祝她下次成功,也不能祝她乐观活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劫难,理解已是奢侈,我没有资格和他人共情。
Day 4
不知不觉过了三天我才开始思考怎么出院这个问题。按照州法律,非自愿入院的患者需要待满72小时才能接受下一步诊断,而医院可以因非工作时间(节假日、周末)等理由推迟诊断,明天就是周末,如果我无法在今天被释放,我至少还要再住三个晚上。精神病院这套程序在过去多年的实践中已经被打磨得非常完备,每日和我们接触的护士和心理医生只是最底层的实施者,而设计和监督系统运行的上层根本是隐形的。被剥夺了外界联系方式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受限于贫乏的信息和护理人员糟糕的管理水平,感觉迷茫和孤立无援才是正常反应。我无法左右最终的决策,但至少可以争取让自己在这里的境遇更舒适些。
我仔细阅读了分到手上的权利义务须知,发现了一些仍可以商议的余地,准备好了每天和医务人员单独会面时的小小演讲。前些天在毫无戒备的面谈里我透露了太多不利于出院的内容,故事还是同样的故事,但听觉效果取决于叙述方式和情绪渲染。见到心理治疗师后我打起充分的精神,煞有介事地记录了她的个人信息,积极地回应了每一个问题,暗示我的入院不过是一个刚到异国的年轻学生在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下造成的误会,强调了我的法学生身份,还有作为唯一的亚洲人在这里受到的区别对待,同时表达了对这个机构可能在程序上违宪的担忧。不知道是具体哪一部分打动了她,我因此得到了每日使用手机一小时的特权,还有格外耐心的澄清。接下来和护士的面谈相比更为艰难,她明显不了解也不在乎病人的处境,只想照章办事守护好自己的工资单。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不耐烦,提出安排医院的法务和我解释。
拿到手机后我和学校取得了联系。和我有私人交往的S教授安慰我说学校可以介入我的治疗计划,前提是我将医疗信息披露给院长和校医,我没有多想就同意了。看着下班时间临近,结合对美国人工作效率的切身体会,我并不抱希望今天能被放出去。
书架上有一本史蒂芬金的悬疑小说《耶路撒冷地》,我试图读了几十页但还没进入情境,Ben像一个散发着笑容的太阳能热源一样席卷而来。我没设想过和一个占尽了优越地位的白人男生讨论类似于换个国家生活这样的问题,有些太过微妙的体察只有某一类人能拥有。Ben听完了我一通关于国际生面临的签证、语言、生活差异问题的牢骚,职业和志业的取舍,政治环境对单薄个体的影响,尽力理解着我的困境,还热情地想着解决办法。我反而更好奇他是怎么来的。他讲述他经历了对CS专业的幻灭后转去了EE,即便每个项目都顺利完成但还是越来越沮丧、茫然、失去动力。他害怕自己走错任意一步都会令那些关心他的人失望,最终引向自毁。在他无比诚恳的刨析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在搬来美国这一年内被迫进行了一系列价值观推翻重塑,失序和混乱下极其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时,我给自己设定了高不可攀的目标和艰难的道路,似乎这样就能万无一失。可我没法欺骗自己,我并不快乐。
和医院法务的交流拨开了我部分的疑虑,即便3天72小时的监禁是法律要求,实践上因为节假日和程序延迟,常规操作是5到7天。疫情前还有亲友探望的可能,现在一概取消了。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我那天深夜自证其罪的供词。如此武断随意的判断标准就足以剥夺一个人3天以上的人身自由,而且经历了多年的法律检验仍运行良好,我完全同意Melissa的看法,社科学生应该来这里做做田野调查。
晚饭时Miguel突然说我让他想起了他曾经约会过的女孩,他们无话不谈,坦白心底的秘密,可惜那个女孩爱他没有他多。我听完心里警铃大作。我说爱上自己的心理医生是很常见的,这说明不了什么。即便后来我们都没有再聊这个话题,但我感受到了异样,接下来打算有意回避和他单独对话。
Day 5
上午的小组活动治疗师介绍了有关抑郁症患者常见的认知扭曲思维cognitive distortion,反思或许我也在无意识中犯过类似的逻辑错误。如果不主动进行协调,任由负面感受堆积膨胀,可以预想自己便会成为自身偏执的囚犯。尤其是对于像我一样的高敏感人群,经常需要处理过载的信息量,识别、归类、有意识干涉自己常有的现实扭曲滤镜其实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技巧。以下简单记录学习内容。
夸大或贬低magnification and minimization:过分放大或缩小事件的重要性,相信自己的成就微不足道,或者自己的错误过分严重。
灾难化思维catastrophizing:只看到最糟糕的结果。以偏概全overgeneralization:从单独或部分事件中得出广泛结论。“我面试表现不好,我总是表现不好。”奇幻思维magical thinking:相信个体行为能够影响不相关的情境。“我是一个优秀的人,这类事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罪责归己personlization:相信自己应该为不可控因素负责。“我妈妈总是情绪不好,如果我多帮她一下她就会变好。”妄下结论jumping to conclusions:没有证据凭空解读事件的含义。
读心mind reading:没有充足的证据凭空解读他人的想法和思维。
臆测未来fortune telling:没有充足的证据仍认为事情会变坏。情绪化推理emotional reasoning:通过情绪推论事情本质。“我感觉自己是个差劲的人,因此我一定是个差劲的人。”否定正面思考disqualifying the positive:忽视事情的正面效果,只承认负面评价。必须思维should statement:认为事情必须向某个方向发展。“我必须保持高效。”全有或全无思维all-or-nothing thinking:使用“总是”“一直”“从来没有”等绝对词思考。“我从来都干不好任何事。”
饭后电视里在播哈利波特,Ben兴冲冲地告诉我昨天他解出了另一组数独,向我展示了厚厚一摞失败的尝试。失去了精神病院唯一有智力要求的消遣后,我们又陷入了漫长的无聊。午后的太阳热烈而生硬,我们坐在室外的长条凳上烤着头顶的炉火。昨天和国内的朋友通过电话又刷新了一遍我对上海的认识。我和Ben说上海已经封城二十多天了,他们的处境显然比我糟糕很多,我实在没法抱怨这里的一切。Ben听完担忧地说,你不应该贬低你自己的感受,你不需要对其他任何人的境遇负责,只要你跟自己之前的处境相比,无论有任何感受都是正当的。他的棕色眼睛格外具有说服力,从这个角度思考确实让我释然。
今天从康复组转来一个神似Tom Cruise的长发小哥,穿着克莱因蓝色卫衣,22岁,从事质检工作。第一天看我光脚走在地上主动送我袜子的德国黑人大叔Derek出院了。已经入院一周多的高中生Abigail仍没等到释放结果。Stenphaun是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跟着前女友从加州搬来GA,分手后女友带着他们的女儿远走高飞,切断了所有联系方式,他无牵无挂就此在GA住下,在学校读理疗专业。Ruben是个23岁的youtube博主,小有成就的摄影师,从小在家接受教育,没上过一天学,他情绪时有起伏,擅长应付小孩子的Melissa总能及时地察觉,设法和他聊天分散他注意力以防造成混乱。我观察着Melissa的行为,她拉我到一边说,你不觉得这些人其实心底里都只是小孩子吗。我点点头,这些无能的工作人员显然并不了解如何和小孩子沟通。她说你真不应该被关在这里,你应该来管这个地方。我连连摇头,这里和法学院相比幸福太多了,我乐意当个病人。
Day 6
出院日期是病友们最喜欢聊的话题,其次便是彼此当下的感受。每一天回答十几遍“你感觉怎么样”类似的问题,我的情绪和感受突然成为了头等大事,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Stenphaun见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略略弯腰问能不能请我喝一杯,我被他逗笑了。毕竟这个地方连多余的果汁都不允许喝,保持苦中作乐的精神绝对是有益于健康的。他转了个圈取来了冰水壶和纸杯,给我们各倒了一杯。我觉得他似乎有话要讲,就陪着他的设定继续扮演下去。他说昨天和Natasha一起打牌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点奇妙的氛围,Natasha感激他的陪伴,还说那是她最近最开心的一天。他说Natasha真的很特别,和其他女孩都不一样,他觉得他遇到了对的人。我惊叹不已,鼓励他继续讲下去。聊起感情,他问我恋爱里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说“健全的人格、沟通的意愿、共同的兴趣”,他想了想,对他来说一定是“很多的沟通,很多的性”,性太重要了,他没法随便给任何人,一定要温情脉脉的拥抱,甜言蜜语,很多爱才可以。他边说边沉浸地表演起来,抱起双臂哼着小曲。我忍不住吐槽说你能想象冷酷的Natasha做出这些举动吗,他激动起来,说他真的希望她可以。
体育馆的官方名称是”康复之路“,一个简陋的球场,几张桌子,提供篮球、橄榄球、瑜伽垫,和一些无害的桌上游戏。前天那位很好说话的心理治疗师和我展示了她正在做的记录,原来工作人员时刻都在监视着病人对日常活动的参与度,并就此进行评估。手边刚好有水粉画笔,我用生疏的书法写下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Aubery打完篮球好奇地探过来,听完我的翻译后说真美。
吃晚饭时有机会和Natasha聊天,我试探着问她是否发现有人在注意她,她一语道破她对Stenphaun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发展其他感情。她接着反问我难道不是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惊讶于她的观察细致,叹了口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地方、这个时机并不适合。
Miguel再次来找我时,提到出院后会为我写歌。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不希望进入互相救赎的关系,不论是友情还是其他,出院后我不会联系他,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只限于这里。他离开了,我也感觉长舒一口气,和Natasha心照不宣地苦笑了一下。
拒绝了Miguel之后我感觉不太好,被Natasha拒绝后的Stenphaun也闷闷不乐,我们坐在走廊远离人声的地方想着自己的心事。他突然说“我总是太快陷入爱情,每一次,我是最忠诚的那一方,可她们最后都离我而去,甚至不会告诉我为什么。我以为她就是那个对的人,可没想到这段恋情只持续了两天。“我说缺爱的人都会这样,但那种感觉不是爱情,只是自身幻想的投射。他说他只是想要爱,想要家庭,可他得到的总是伤害。我感到一阵悲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些人天生就有的东西,另一些人要穷尽一生去追求,命运的作弄鲜有公平一说。而一旦有了对外界的需求,执念和痛苦便会滋生。欲望本身让我们画地为牢。
Day 7
今天是周一,工作日,按照日程治疗团队会召开集体会议讨论每个人的出院结果。Ben的家人已经从V州飞过来接他了,午饭后他向队列里的每一个人道了别,祝福了我美好的前程。接下来我也得到了出院通知,和病友们一一拥抱,给Miriam留下了亚特兰大几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资源,希望她早日救出女儿。
不知道是药效还是这段精神突围,曾经时刻困扰我的剧烈情绪起伏逐渐趋于平缓了,原来当个正常人的感受是这样的。对心理疾病的轻视和忽略阻碍了我及时进行治疗,这么些年我和它的斗争原本不必那么坎坷。我感觉坦然、释怀和安全。我不再期待运气和因果在某刻终于会眷顾我,也不再害怕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无常将我抛回持续的动荡中,因为我清楚自己有承受破碎、重力和震颤的韧性。护士合上了我厚厚的档案,带我穿过重重铁门,再一次感受到清风拂面,南方春日翻涌的气息如此陌生又如此崭新。生活不过是长久的疲乏和失意中夹杂着细碎的片刻欢愉,哪有永恒的崇高和纯粹的美。远观地球的旅居者们的活动,拆解开来无非是进食、休息、娱乐和谋生的组合。自洽于某种有限的偏颇,接受了某种使命的说辞,发展出一套足以欺骗自己的理论,就能过得去这一生。
上一篇:给我赵雷的(赵雷的偶像是谁)
下一篇:没有了